常聚长兴微信平台正在推出由中国作家张加强著的文化大散文《近在远方(一个县的史诗)》。本书共有四个篇章,分别为“脚印—与看不见的声音独语”、“街巷—让阳光照进历史的屋子”、“地气,用最世俗的方式爱你”和“留痕—学会赞美黄昏”。
今日为大家推送收录在“街巷—让阳光照进历史的屋子”篇章中的三篇文章:下箬,那一口圣井、陈故宫,那前世未了的心结和天居寺,用作后世审判。

下箬,那一口圣井
古井深幽,默不作答。妇人放下一只木桶,“扑通”一声,阖启了今人的思绪。古井将历史珍藏,一桶桶地送将上来,又用幽深目光,注视今昔,别来无恙,放心了闭上眼。
古井孕育了世代的下箬人,饮水人把古井视为自己的图腾,对古井顶礼膜拜。惊服那光滑如玉镯锃亮如青锋的石围井栏。岁月迢遥,历史的喧嚣已归于沉寂。

西晋永嘉年间,晋元帝南渡。有个叫陈达的京官选择长兴做县令,此人在京城的官职是丞相掾佐,太子洗马,也就是太子侍从官。陈氏南渡第一个落脚点选在长兴,令部属疑惑。陈达说:“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焉,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
陈达子孙经过十世繁衍,也出过不少朝廷命官,一直到陈霸先的爷爷陈道巨,做了太常卿,掌管朝廷祭祀,属三品官员。但陈霸先的父亲陈文赞没出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长兴陈家到陈霸先出生时已从曾经的望族跌人寒门。陈霸先从打鱼为生开始做村干部,后到南京做看守油库的卑微小吏,从村长到将军,再到黄袍加身,一路苦难与衷君,一路风尘与爱民。
皇帝功德,能为后人感动的不多。到了明朝,归有光与吴承恩主政长兴,有感于陈霸先的千秋功业,撰文写下三百字的《圣井铭》,在文中,他以这口井历经岁月沧桑,依然不竭不涸,来颂扬贤帝明主的大业光灿。当时正值隆庆元年,两位才当上七品小官的花甲老人合作了这件作品,少不了要流露出对当今皇上感恩戴德的心情。1979年9月,长兴县为《圣井铭并叙》碑和《梦鼎堂记》碑重建了碑亭。
公元6世纪,是个乱了套的时代。宋、齐、梁三个小王朝,没有一个像样的,朝纲紊乱,自相残杀,生灵涂炭。刘宋发生家乱,杀遍宗室骨,子孙们均不得善终。文帝、孝武、废帝、明帝都在家乱中被自己人所杀。孝武帝的儿子刘子业杀掉了五个叔父和一批大将,明帝又杀尽了孝武帝的十余个儿子,还把自己的四个弟弟杀了。到了齐,明帝也学了这一手,杀尽高帝、武帝的十九个儿子,其惨毒自古未有。中国宫廷残暴丑恶的本质,在南朝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霸先在位三年,陈家三世五帝为历史浓缩了诸多精华。他的侄子陈蒨接过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偏安局面-巴蜀、汉中是北周的地盘,长江以北为北齐所占,岭南、江西、福建也为人割据。
陈朝面临的劲敌应该是西魏和后起的北周,而不是北齐。历史的错位就在这里。陈本应与北齐走到一起,以稳住这三国鼎立态势,因为周放回了人质宣帝陈顼和儿子陈叔宝,可结果陈却与北周联合去对付北齐,轻松从北齐手中拿回淮南之地。然这一胜利帮了北周的忙。北周借陈朝的灭齐,三国鼎立的态势顿失,陈朝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宣帝陈顼在位十三年,身边缺乏一位能够分析天下大势的军师,不善连横,以致划淮而守,四面招风,八方树敌。
陈叔宝有治国之才,水平也不亚于前几位先帝。他亲政之初还是很敬业的。此时,江对岸的隋文帝杨坚虎视眈眈。陈朝犹如栖息在虎穴旁的山兔,天地虽美,性命却掌握在他人的好恶之中。
北方磨刀霍霍,陈朝的灭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自东晋偏安江东以来,祖逖、庾亮、殷浩、桓温皆曾北伐,都没有成功。依陈国的实力,统一北方根本不可能,明知打不过人家,不如不打,让江南人过个安定日子,也是哲学一种。
在建康,曾有宫廷多“怨井”之说。隋军杀人宫中,陈叔宝与张贵妃、孔贵妃三人抱作一团躲在井里。陈灭,皇族随陈叔宝人长安。隋帝本与陈家无怨,于是对陈家族人采用宽容政策,陈家根脉得以继续繁衍,这也表明了陈叔宝的明智。陈氏下箬里“圣井”恩泽长存。
江南的古井直通历史深处。井不管深浅,只要常用,定有碧水,只要细究,必有经典。井的传说与故事,屡屡验证江南乡间为何藏魂。
石块砌成井壁,布着青苔,石缝间生一株株细草,有草必有水,有水则清则凉则有淡淡的甘味。青苔细细密密,把所有的故事封存起来,水面无波,天光云影,任它自由来去。时间的分量,让这旧色时光变得凝重、深长。
圆圆的井圈,是古时的眼睛,幽幽的,注视着过往与现在,另一藏在井里的,是目睹历史过道里血雨腥风的日子和诗天画地风雅飘逸的南朝。
陈故宫,那前世未了的心结
下箬遗址公园,建有陈家祠堂,也叫陈故宫,供着陈族曾经的辉煌人物。陈霸先为最,一个霸字,注定名播天下。历史上占了无数春秋的帝王,留下好名声的不多。陈霸先三年皇帝,落个英明,已是翘楚。

江南人家,淋过南朝的腥风血雨,闻过两宋的金戈铁马,涉过明初的穷恶山水,舔过清初的毒镞血刃,劫后的意识形态,留下末期政治的文化遗民,故而不时讲个骨力。
三十三年的陈家王朝,于历史的存在,当在一武一文。武帝陈霸先,先忠君后德治,一身正气。文的,自然数陈叔宝,但一直遭后人诟病。
东晋和宋齐梁陈在秦淮河畔匆匆过后,第一个问罪者是李白。李白过金陵,愁上心头,一见秦淮河的绿水、玉琴,便寄愁诗一首。杜牧、李商隐则激昂,干脆把亡国账记在这温山软水上。清代诗人黄仲则“杜鹃声里过秦淮”,也忍禁不住“回首南朝无限恨”。游过秦淮河的,大概都有这种薄薄的怨恨。
历朝亡国之君,就才能而言,陈叔宝在李煜赵佶杨广之上,李煜葬送了南唐王朝,留下一些招魂曲当在情理。陈叔宝处偏安时代接过祖上这笔烫手的财产,已很难经营了。他眼里,做诗度曲才是正业,管理国家不过是他偶一为之的“副业”而已。
后人攻击陈叔宝的,两件事:一是他的诗曲。艳冶轻薄的诗,还能谱曲,《玉树后庭花》的曲调,成了靡靡之音的代名词。二是美女误国。“商女不知亡国恨”。张丽华眉目如画,发长七尺,黑亮如漆,脸若朝霞,肤如白雪,陈叔宝爱不释手。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杨广见到这位“长发过膝,倾国倾城”的吴兴美女,“欲占之”,张不从,引颈自戕,殉陈。血写了秦淮河畔第一个殉情故国的悲壮。
陈叔宝才气横溢,不是一个羸弱文人,那首“寒去轻重色,秋水来去波。待我戎衣定,然送大风歌”别出一格于艳靡之外,颇具汉高祖刘邦击筑而歌《大风歌》的丈夫气概。《玉树后庭花》被称为亡国之音。其实历史自有其向前的步伐,无论陈后主写不写亡国之音,隋文帝杨坚的一统大业还是要实现。陈后主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行。
陈叔宝的诗现存九十首,极具艺术技巧,对后人很有些影响力。初唐的大诗人们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首先效法。他们的艺术心路源于宫体诗,王世贞所说初唐四杰“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
宫体诗是唐诗繁荣之源,陈叔宝是一面旗帜,文化传承的先驱。唐诗里有一名作《春江花月夜》。该诗见哲理,见时空,寓短暂于永恒之中,作者张若虚以一诗流芳,闻一多说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
其实张若虚只是一次再创作,这诗的原创是陈叔宝,两诗相去不多。人们只知道陈叔宝《玉树后庭花》传世,其实他的《春江花月夜》也很不错。隋炀帝杨广看到后,见此诗入味,便使尽解数,也作一首《春江花月夜》,但不如陈叔宝。最后,倒是让张若虚坐收渔利。
不为他人制造悲剧,就是在为自己创造幸福。人本不是为什么名分活着,一切名、义都应是为让人们活得更好。李贽曾用“社者,安民,稷者,养民”之理,称赞五代时历事四姓十二君的冯道和三国时劝刘禅开城投降曹魏的谯周。他们不是把一姓一主的荣辱放在至上的地位,而避免让百姓万民无谓地受锋镝之灾,只可惜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总不在正统。
今人的认知范式还在更旧的世界或更古远的歌调里。江南是一方种什么长什么的水土,一方聚财生息的水土,一方让财富提升为精神的水土,灾害与萧条惟这方山水可以化解。
生命仅仅是一个瞬间,瞬间留瑰宝传世,常人难以为之。陈叔宝凭他的贵族气质,成了中国帝王不设防的先例。
天居寺,用作后世审判
在天居寺走近佛教经典,一位女居士说两个办法:
一种如读楞严经,须逐字逐句理解其意,为此要借助诸多外援,在大脑里盘旋许久。
另一种就如诵法华经,跟随专业念经的法师们的速度,无停顿无思索,任字音于舌尖滑过而不求甚解。这后一种方式于我这爱“咬文嚼字”的人特别新鲜。
天居寺这一日读下来,平静愉悦。

也许“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也许其义不现也不重要,因为如果目的是“降伏自心”的话,解确实有助于降伏,即或不解,却能致心一处,亦是一种降伏。
拜天居寺,多半是跪陈武帝。史家对陈霸先的人格力量评价甚高,前比刘邦后比李世民。清人赵翼评价陈霸先“虽偏安江左,亦有帝王之量哉”。
陈朝演绎了另一个三国。战争与谋略、人才与鬼才、奔袭与静候、忠诚与弑君,一幕幕悲喜剧、正闹剧,让南朝的大河在地面消失,转为精神的暗河,留作后人数落。陈霸先成为北齐、北周鼎足而三的一国之主。唐太宗的谏官魏徵佩服,说陈霸先鼎峙之雄,绝不在孙权、刘备之下。
陈霸先为陈朝开了个头,便撒手西归,他的侄子陈蒨受命于危难之际。陈霸先崇佛,继位的文帝陈蒨创立了规模宏大的药师斋忏仪式流传,撰写了“药师斋忏文”。陈文帝在家乡长兴西为皇考始兴昭烈王太妃建“报德寺”,以供奉药师佛和举行药王斋忏水陆法会。陈霸先常对人说,此儿是陈家英秀人物。然陈蒨接过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偏安局面,可惜这样一个开明君主只活了四十五岁。
陈叔宝并非隋炀帝所说的“全无心肝”。他比谁都清醒。依陈国的实力,统一北方根本不可能,自己有多少善战将士他心里清楚,让江南人过个安定日子,也是哲学一种。
陈后主亲政之初,史书评价其“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奖励垦荒,禁止奢靡,擢用廉吏,关心民瘼,采纳忠言谠论”。说明陈叔宝有治国之才。
隋文帝大举南伐,陈后主竟临危不惧,说:“王气在此,齐、周数次南伐,无不摧没,虏今来必自败。”豪气冲天。当杨广的部队兵临建康城下,陈军四处溃散,陈叔宝下旨给大将们“为我一决”。虽为时已晚,还是很沉着的。
据《中华姓氏通书》记载,陈灭后,陈氏先后有几脉去了福建、江西等地。其中陈叔宝的弟弟陈叔明的后人陈旺一脉,去了江州,具体应在今天江西九江地区的德安太平乡。
广东作家陈启文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江州义门》,封底有这样一段文字:
江州义门,堪称是中国社会史一大奇观。
陈朝灭亡后,陈皇室后裔一支迁徙到江西德安太平乡,由一人发展到三千多人,缔造了一个“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家族社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公有制社会形态,比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理论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构想早了数百年。江州义门历经唐宋元朝代更迭,处乱世或盛世之中,以“义”字为信念,齐家、修身、治学、立法,建立一套成熟的公有制社会模式,安世三百余年,直至被封建帝国强行瓦解,分崩离析为291庄,分别迁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安徽、上海等地,因而有言道“天下陈姓出江州”。
当然,后面还有“江州陈姓出长兴”之说。史载:“十九代同居共饮”,有田庄三百人多处。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大臣上疏建议分析。不久,皇上下旨,派员监护分析陈氏。陈氏家族由此分布全国。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兵败后又有一次大分析,这是中国家族史上的一大奇观。
因为陈叔宝的拱手相让,陈姓族人逃脱了被斩尽杀绝的厄运,陈氏大树继续根繁叶茂。陈叔宝如此功德,天下陈氏后代应在这位祖先牌位上作虔诚一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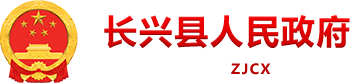

 旅游动态
旅游动态